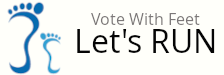01-05-2024, 04:10 AM
这是一部从头到尾都很平静的电影,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恨情仇,也没有突出的高潮。在这个人来人往的殡仪馆里,所有的死亡被最大程度的稀释,每一个人都安静又普通。
这也是一部献给普通人的电影,以普通人为主角,在普通人的视角下唤醒从失去中获得珍惜眼前人的能力,无论是与他人郑重地告别,还是与自己认真地和解,都是要尽力不留遗憾。
老陆和闻善有一段对话,大意是说:
普通吗?好像不。那不普通吗?再不普通的人,和他待久了,好像也没什么不普通的。
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写照啊。
作为一个出入殡仪馆替亡者写悼词的人,普普通通的闻善存在感从来都很低。不出事的家庭不愿提起他,出了事的家庭不能尊重他。
不辞辛劳地奔走在亡者的各路社会关系之间,兢兢业业的责任感却被委托人没好气地戏谑成“你还挺麻烦”。事毕之后,并不会邀请他参加追悼会,但在委托人心里不管事情已经结束了多久,闻善依然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打扰的人。
但就是这个可以被打扰的局外人,却因为写悼词而成为了最了解亡者一生的人。
又正因为他的了解,给这份随意打扰第三人的自私行径扣上了一顶正当的帽子,多少有些令人哑然。
海报上有句宣传词,“别等只剩一纸悼词,才想起陪伴。”
影片里有一对祖孙三代。儿子在忙碌的工作间歇与闻善插空谈起过世的老父,就是一幕幕父常念子、子却不知父的场景。父亲曾言“人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儿子浅薄地想当然化父亲的行为,殊不知那些竹子代表着父亲的精神世界。
他寄望的绿竹和家乡的远山,其实是在无言地渴求着能和儿子有一些交流。被他挂在嘴边的不仅仅是那些竹与山,更是曾经在那个被竹与山环绕着的世界里没有走远的儿子。物质可以不丰饶,但精神不可不富庶。这些儿子没有留意的细节,年幼的孙子却尽收眼底。导演给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,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血里的一句老话——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而闻善一句“王先生作为儿子已经翻篇了,但作为父亲还有很长时间。”却给老话增添了新的注脚。
随着电影里的故事发展,忍不住会问自己真的了解身边以为很熟悉的人吗,我可以滔滔不绝地对某个人的整体形象侃侃而谈吗?
人有很多面,我能看见的仅仅是千分之一面。
但至少应该对这千分之一面如数家珍,方不失为子女与挚友。
而当一个人的形象看似通过你我他之口正逐渐立体起来时,还是突然会在某个时刻发现其实缺了一块拼图,是ta自己的那一块,那个被ta藏在心里的自己。
电影里有一句话是朋友调侃闻善的,说总是习惯了独来独往的他,“单枪匹马的走不远”,这叫做“拒绝进步”。
离群索居者,不是野兽便是神明,所以人是社会型动物。
孤独多年的闻善通过书写观察日记,在形形色色中穿梭,那呕心沥血写就的一张张悼词是渡人也是渡己。在电影的最后,有了姓名、不再穿毛衣戴帽子的小尹消失了,闻善也终于迎来内心的曙光,找到身为落魄编剧他搁浅多年的剧本得以继续创作的行文方向。
只有一个人主动地补上了自己藏起来的那一块,形象才可以称得上是完整。
既然活过,总该是得要留下些什么的。
若能不虚此行,便也不枉此生。